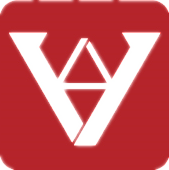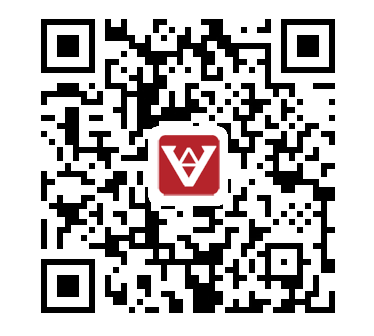破解会议记录玄机 一字定乾坤
2006年4月3日一大早,F和小F父子俩人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国刑警学院的大门,他们刚从香港飞抵沈阳,是慕贾玉文教授之名来做鉴定的。他们知道,贾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文检专家,曾因为“亚洲第一富婆”龚如心的世纪遗产争夺案胜诉提供关键证据而蜚声海内外;他们要鉴定的是一份仅有三页的会议记录,而就是这样一份小小的会议纪录,却使两个家庭反目,陷入长达九年的纠纷之中;为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贾教授身上。
在贾教授的办公室里,他们用并不熟练的汉语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诉说了案件的始末。
一份扑朔迷离的会议记录
十几年前,香港的谭女士创立了一间幼稚园,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发展成一所小有名气的连锁幼儿教育企业。期间,谭女士的丈夫(F先生)、妹夫(C先生)也逐渐进入管理层。1997年,谭女士带着18岁的儿子(小F)离开香港,去加拿大定居,企业便由F先生和C先生分别管理。
1998年,当谭女士返回香港后,她发现C先生管理的企业内部财务极度混乱,但由于精力有限,无法进行清理整顿,于是提出分家,各自经营自己分管的幼稚园。根据该公司1997年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最末条款,C先生需定期向企业的发起人——谭女士交纳相应比例分红。该董事会会议记录共有三页,经复印后,与会者在原本和复印本上每一页均签名认可,并由双方各存一份。C先生保存的是手写记录的原稿,谭女士保存的是会议记录的复印本。但是,C先生却对会议记录中有关分红规定的条款提出质疑,声称本没有此规定,谭女士持有的会议记录第三页所载的这一条共4行字是后复印添加上去的,而自己保存的那份会议记录原本已无处查找。双方就此反目。
受理鉴定,蛛丝马迹尽收眼底
在办公室里,贾玉文教授在仔细倾听了F父子的讲述后,接过了小F递给他的会议记录。小F指着会议记录第三页上的第6至9行文字对贾教授说,只要能证明这四行文字不是复印插入的即可。
交到贾教授手中的会议记录共有三页,均是复印形成的。每一页上面记录内容都是手写文字,并且在空白处有多人签字的原本,参见附图。贾教授拿起放大镜,对会议记录进行仔细的检查,每一页的文字笔画、空白处、签名处……他都认真进行研究。当他看到第三页的第8行文字时停了下来,思考片刻后,问小F可有C先生书写“费”字的笔迹样本。经确认会议记录上除这6-9行文字外,其它字迹均是C先生所写后,贾教授表示可以受理这起案件。
贾教授认为,如果在会议记录复印件第三页空白部位加插一段文字,最方便的办法是将拟好的文字内容(原稿)置于复印机上,经实验调整好位置,然后再复印到复印本第三页的空白处;另一种办法是用扫描器将文字图像存入电脑,再通过打印机打印到复印本的第三页空白部位。鉴于会议记录第三页的具体特点,比较第1-5行与6-9行的印迹,采用电脑扫描打印的可能性很小。
基于上面的思路,贾教授采用排除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做出检验:可能出现的复印插入特征没有出现;第三页无再次经过复印机的特征;第三页第8行用圆珠笔添写的“费”字是C先生所写。据此,贾教授在的报告中明确得出,会议记录第三页之6-9行字迹不是复印插入的(在C先生添写“费”字之前已有),并于4月14日出具了鉴定书。
4月29日,C先生一方委托香港黄恩赐博士鉴定并出具一份《笔迹鉴证报告》。黄博士的结论认为,受质疑之中文字“费”不是C先生所写,不能排除第6-9行笔迹是以剪贴加重新复印的方法插入的可能性。贾教授收到黄博士鉴证报告中文版后,针对黄博士的观点和结论,2006年8月12日又出具了补充鉴定报告,坚持原来的结论,并对黄博士的论据和论点作了有力的批驳。
成竹在胸,再创完美法庭辩论
2006年11月25日,贾玉文教授按照委托人的通知,赴香港准备在高等法院出庭作证。经过六年前作为“世纪遗产争夺案”专家证人长达37天的磨练,如今再次在香港高等法院出庭作证,贾教授觉得完全可以轻松应对。
11月29日,C先生一方聘请的鉴定专家黄博士首先作证,他复制放大了贾玉文教授鉴定书“费”字的比对表,说明会议记录中“费”字与C先生的笔迹的三个最重要差异,即分别是费字横画的形态、“贝”部竖与横折笔的折回画、字形比例上具体数值的差别。黄博士口才非凡,让在场的F父子着实担心起来,紧张地将目光投向旁听席上的贾教授,但贾教授神态自若,令他们的心情慢慢平稳下来。
11月30日15:55贾玉文教授出庭作证。在听到法官的传唤后,贾教授从容镇静地走向证人席。在证人席一侧摆放着高倍实体视频显微镜和光源,这些设备都是为他专门准备的。首先,他将自己做的实验材料呈给法官,其中包括一次和多次复印件底灰的比较材料;签字压痕经复印机前后的对比材料等。他用显微镜演示了实验材料上底灰与复印次数之间的关系,并陈述说:如果这四行文字是后复印插入的,那么会议记录的第三页必定要比前两页多一次走过复印机,第三页上的墨粉底灰必定比前两页浓重,而且第三页上签名的笔画压痕由于受复印定影装置的碾压作用会被压平,从而表现出与前两页签名压痕的明显的差别;之后,他将会议记录上三页纸空白处的底灰和每页上的同一人签字的压痕一一显微放大并在液晶屏幕上显示出来,令在座的女法官禁不住走下台来仔细观看。当她看到会议记录第三页的复印底灰和签字压痕与前两页并无差异后,点了点头。
接下来,贾教授针对黄博士作证时提出的“费”字的差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说:“C先生作记录时字写的较大。会议记录原稿复印之后添写的“费”字较小,是因为受狭小的空间限制造成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在不受限制的纸面上书写时,书写运动流畅,尤其是会议记录书写速度快,书写运动不受约束。但如果事先规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进行书写,落笔时就比较小心,书写运动受约束,显得拘谨、放不开,书写速度也必然要减慢。因此,“费”字字形上的差异是由于书写条件造成的,不是不同人书写的本质差异。”
贾教授进而指出,黄博士用画线和测量的方式来说明争议的“费”字超出了C先生书写的“费”字的变化范围,但黄博士所使用的样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且在黄博士没有采用的样本中,用画线和测量之法还可找到几个比例变化更大的“费”字,因此,贾教授对法官说:“一个人写字具有自然变化,根据有限的已知样本来规定它的变化范围是不可靠的。”“黄博士讲的‘费’字横画差异,实际上是由于下笔比较小心,书写速度比较慢,以楷书的笔法写这个横画造成的。”贾教授又在C先生笔迹样本中找到相似的笔法,并当庭进行了演示,以此证明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差异。贾教授在法庭上娓娓细说,在场的人都不时地点头称许。
次日,C先生一方大律师开始盘问贾玉文教授。对于可能被问及的事项,他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是,对方律师精心设下陷阱,出其不意的问题考验着贾教授的学识与胆略。大律师拿出庭前准备的会议记录的复印件,问贾教授:“你检验的会议记录与这个复印件是不是一样的?”贾教授回答“是。”律师诡秘地一笑,接着问“会议记录的正本空白处的中文字,在复印件上没有了,是不是?”“是的”,贾教授沉着而坚定的说:“但这是因为多次复印造成的信息损失,虽不能看出完整的字来,但残存的笔画依稀可见。”
律师刚刚做出的笑容顿时变成了僵硬的尴尬表情,他立刻转变话题,针对会议记录上订口和订孔的印迹,准备再绕圈子下套。谁知,贾教授非但没有上当,还使律师对自己的提问都不明所以,引来了法官的训斥。律师红着脸,擦了擦汗,接着就黄博士指出的三个重要差异点继续盘问贾教授。
贾教授听完他的叙述后说:“‘费’字横画的所谓巢形、‘贝’部竖画向内弯和折回画与样本字不是完全一样,这是笔迹的自然变化。正如一个人连续写的几个字,每个字都不可能完全一样,都会有些差别。在文件中出现的两个‘费’字之间也存在这种差别。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差异,而只是小小的程度上的差别。如果把这小小程度上的差别看作重要差异,那世界上的所有字就都不能说是本人写的了。”
贾教授有理有据地回答了律师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后,律师显然已经没有信心再盘问下去了,他最后无力地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虽然我们认为黄博士讲的都正确,但你肯定认为黄博士讲的都不正确,是吗?”贾教授笑了笑说,“不能说他说的都不正确。他有些话也是对的。”贾教授谦虚的回答赢来了法官和在场旁听人员敬佩的目光。
贾玉文教授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精湛的鉴定技术和近乎完美的法庭作证,结束了两个家庭长达九年的是非恩怨,又一次在香港最高法庭上为内地文书鉴定人赢得了声誉。
案例来源:中国刑警学院 贾玉文 崔岚 张洪星
编 辑:广东开元文书司法鉴定所 王世全 李晓庆